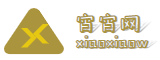彼时彼刻全章节小说阅读

“姐,你在这干嘛呢?母亲说你病了,大夫如何嘱咐?”顺手把狐裘盖在了她身上。
她睁开眼“没事,普通伤寒而已;只是近来得忌口。”她笑着说。
“倒是你啊,一天到晚只知晓胡闹;别总让母亲忧心,明白否?
“呃……我说姐啊,你一个小矮子除了欺负凤你会干嘛!你就不要瞎操心我的事啦。”
“你还知不知道我是你姐啊!死小子,看我不揍你!”
“就你这样谁还敢娶你,披头散发的懒女人!”她直勾勾的盯着若晖“…呃…那啥,啊烯还等着我呢,我走了”一溜烟消失在她眼前。
这是风州,这里的人可以选择自己所爱,不论家世不谈权势——当然,这只是对少数风州人而言。
她叫若夙,生性直白、且爱憎分明。
遇见他的时候,她尚且年幼不懂情爱,只莫名眼睛追随着他。
六年,直至他音讯杳无她才下定决心。
再见的时候,必将倾心以付;诉尽衷肠。
世事难料,后来诸多变故,那人从此也便就从她心里抹去了。
听说鲛人一生挚爱一人,为一人取其性别;为一人决其生死。
可若是,所有的努力和爱慕都只为了那场注定变成泡沫的悲剧;到底还值不值得?
她素来活的自在,此番没了惦想愈发的嚣张自在了;枕着寒庙里的山石看着流云变幻,定定的想着什么。
“嗨!”有人突然朝她喊了一声。
她被吓了一跳,翻身落入了池中,一池的锦鲤被吓得四散;她忍着满身怒气从莲池里站起来,扫了一眼岸上男子顿时怒气消了个干净。
“乖,看在你长得这般好看的份上;就要你以身相许便轻饶了你罢,如何?”话间把湿了的长发撩在肩膀后头,向岸上的男子抛了个媚眼。
男子惊颤之余不知该如何回话呆在原地,期间有人慢步往这边过来;若夙听出是父亲的声音,立即提了湿漉漉的裙摆爬出了池子奔得老远。
只余下那男子,在风中凌乱……他勾起唇。
有意思……
若夙平日里便是个真真正的懒姑娘,此番落了池子生了风寒;便愈加变本加厉,日日缠着凤给她找好玩的好吃的。
偏凤也是好欺负得很,听她说什么便是什么;被她爹抓了,便更是义气一己扛下。
此番她拉着凤,说白日里遇见的男子;长得怎样好看,如何漂亮;全然不曾发觉凤不自然的回应,失落的表情。
夜里起了风,帝凤翻进她的窗子;在她的腹部位置放了暖袋为她捻紧被子,轻轻地合上了窗。
最幸福的事,是你喜欢的人刚好喜欢你呢。
帝凤坐在木樨树下,苦笑一番看着那轮明月;扯过腰间的酒一饮而尽。
她又做了梦,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尾鱼;拼命的游不停的游。
却不知道为什么,只觉得不能停下来。
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窗格里撒了进来,她揉了揉眼睛伸了个懒腰,一个蓝色的暖袋从床上掉了出去。
她赤着脚踩在白色羊毛毡子上头,捡起案上的梳子;梳好了也不束发,披着头发开了门,由着慵懒的阳光洒在脸上。
他看得恍了神,跳下梁子无奈的说“就算是翠儿请了假你也不能不束发啊!好歹你也是若家大小姐。”
“平日里看你看得惯了,没想到我家凤;比任何一个男人都漂亮啊!”她看着他羞红了脸,像个痞子一样调戏他。
他别扭的把她扳过去,“那是你笨!”他拿起案上的梳子,生涩的为她綰了个不算漂亮的头发。
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颠沛流离,在情爱里迷失;在得到与失去之间仿徨,在……他看不见的地方想念。
若夙自觉活的通透,不曾想总是在爱上一个人之后迷离痛苦。
“笨蛋、傻瓜、白痴。”
若夙挠着自己的头发,碰倒了妆奁,珠翠迤逦了一地;她颓然趴在梳妆台上,墨色长发撒了一桌。
窗外头的木樨花树,落下几片叶片慢慢铺在红泥上;像极了一朵凋零的木樨花。
怎的这副模样,这就得从几天前的风州节戏说起了。
七月中旬风州集其他八州,九州同集在风州做一场***。
今日的风州自然是比以往的节日还要热闹。
这日风州节戏,若夙早早的起了床;散着长发跑到琼台边的木樨树下头,戏台还不曾架好,她就已经在树上打了个旽。
台上才起了唱“金陵玉殿……”这厢没出息的就被惊醒了,从木樨树桠上掉了下来,且悲催的被树枝划破了衣裳和手臂。
这厢在半梦半醒间,被树下一个玄衣男子接住了。
她糊着睡眼看着男子,以为还在做着梦轻佻的勾起男子的下巴,“呜……怎的看不清明呢,乖!别动。”
猛地,这糊涂态的若家千金似乎想到了什么挣脱了来人的怀抱;尽量维持着所剩无几端仪,低下头行礼答谢的期间狠狠的揉了揉眼睛。
恰到好处的笑着答谢,来人一身玄色衣裳,纵她平日如何顽劣;她也是知道的,玄色是王族才能穿的衣裳。
九州有九个王,她的父亲便是风王;而此人衣裳上的纹饰绣着流云变幻,分明是幻州王族。
在她沉思间,来人抚过她的头发;去掉了头发上头的枯枝落叶。
她抬起头,看见一双琉璃色的眼睛和灰蓝的长发;怔愣了片刻对上了他的眼睛羞红了脸;忙低下头。
高台上唱着“俺曾睡风流觉,将五十年兴看尽;残梦最真,旧境难丢掉……”;若夙的脑子一片空白;久久回荡着台上曲子。
这厮一回去,便又是笑又是疯的缠着凤讲着日里遇见的男子。
凤头疼的揉着脑袋,“这是你这个月里调戏的第几个男子了?再怎么不济你也是风州若家千金,你何时才能顾及风州颜面;如何再能由着你荒唐胡来!你若再不听我的话,我就离开这里!”